原著:Konstantya https://www.fanfiction.net/s/6535915/1/White-Horses
授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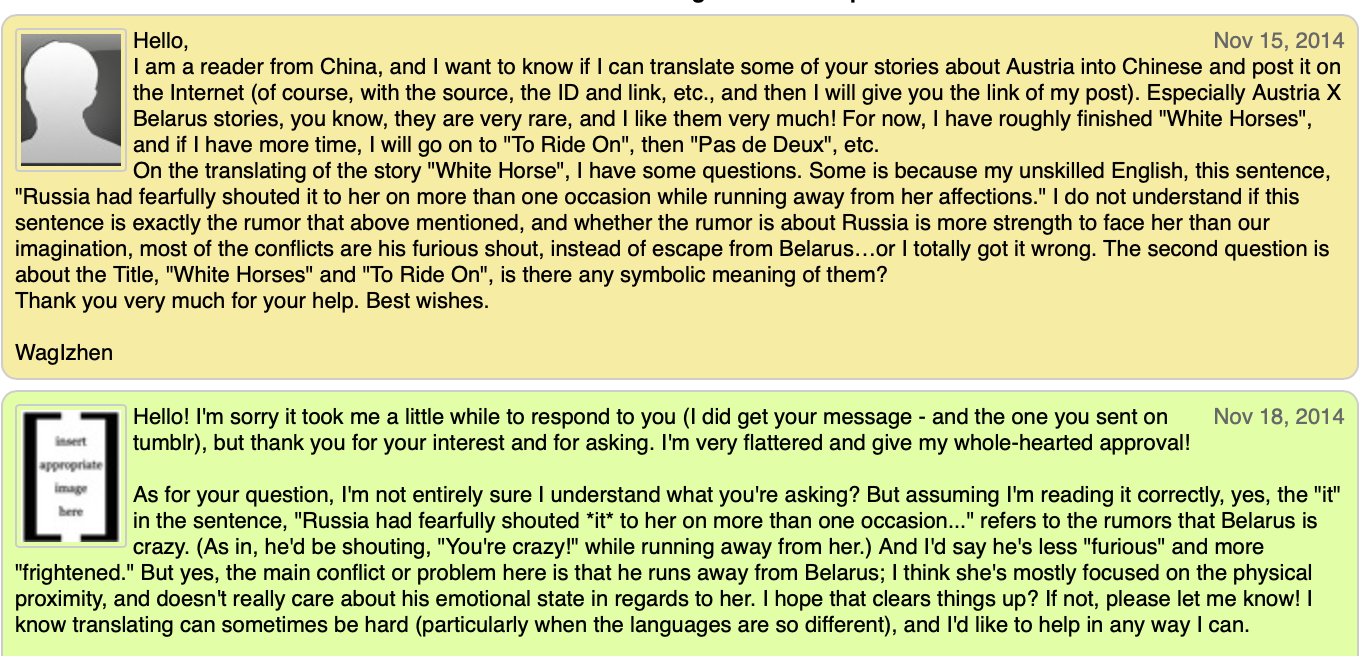
警告:这个小说有很强的BD艾斯爱慕主题。这有一点色情,如果您猜不出来的话,但是它确实是有些与情节相关的色情(我是这样希望的DX),因为情节对我来说总是比单纯的性要重要。不管怎样,如果它由于这些内容被锁了,请在我的LJ找到它。
免责(但是根本上没用)CYA:它不属于我。
剧情梗概:对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几个世纪无法得到回应的爱,会使女孩子们做出有趣的事情。奥地利X白俄罗斯。(现在有了续集,“To Ride On”)
她第一次真正地注意到他的时候,是在1992年的圣诞节。
在距离“铁幕”倒掉不久的时候,比利时举办了这个节日聚会,这是由于她的首都恰好是北约的总部。美国和俄罗斯都收到了比利时强硬的信息,她说她知道,冷战的紧张并未完全由于苏联的解体而消解,但是她希望他们在这个晚上能够有良好的表现。
结果是,比利时应当省着些力气去对付法国,因为后者喝了稍微多些的红酒。他还奇迹般地穿着大部分的衣服,于是继续去摸索着狂饮作乐,似乎要弥补他并没有裸着的事实。在这个晚上,一本正经的奥地利看起来特别地受到他到处游弋的手的喜爱。
第一次的时候,他清醒着。他尴尬地红着脸紧张地把法国的手推开。
第二次的时候,他喝着一杯红酒。他没脸红,而是更用力地把法国的手打了下去。
第三次的时候,他喝了至少四杯啤酒,是被普鲁士硬灌下去的。最终法国倒在地板上被一只靴子踩着肩膀,他的胳膊在他身后扭着,同时奥地利严肃地在为他的行为是多么的不成体统和粗鲁——特别是作为某地的客人的时候——而谴责着他。
德国非常正式地向比利时道歉,并小声地说着一些有关与日本的良好关系的事。意大利则高兴地表示这和武术毫无关系,并且提到了奥地利在他小时候捣乱的情况下就是这样对他的,除了没有扭胳膊。他的哥哥拍了一下他的后脑勺,并酸溜溜地提醒他,失败的革命不是什么值得快乐地回忆起来的事情。
她知道,他曾经是个帝国。她也曾经是,和俄罗斯一起,然后是和立陶宛一起。
他们的历史并没有真正直接地交集,虽然他曾与他的哥哥保持着不止一世纪的良好关系——当他去圣彼得堡拜访俄罗斯的时候,那是她唯一一次真正地看到他。
那是匆匆一瞥和转瞬而逝的印象:热爱音乐,总是得体但却保守的服装。他观看了芭蕾舞,并在喝伏特加时呛到了。当在被允许进行对话的时候,礼貌地对她说着话,而她则是轻蔑地忽略了他,因为他本来就是可以忽略的。他有着弹钢琴的柔软的手,纤细的骨架,怎么看都不会是一个战斗者,一点都不像俄罗斯。
这样一个国家是怎么从十五世纪开始就保持着一个帝国的领头地位,这完全超越了她的认知。她经常将其归因于某些奇怪、政治上的侥幸。
一些年之后,圣诞节的聚会在奥地利那里举行,她和她的哥哥姐姐来到了维也纳。因为他们的经济还不是不够好,所以需要尽一切努力来省油和省钱。俄罗斯开着车,她安静地坐在副驾驶座上,长时间偷偷地看着他。乌克兰坐在后座上,勇敢地用发抖的声音担任起缓和气氛的作用。
他在门口问候他们,并把他们引向餐厅。酒足饭饱之后他们来到了休息室。英国在和丹麦在打台球,西班牙搞着一些音乐,波兰则拉着她的姐姐跳一些民族舞蹈。夜晚的时间缓慢地消逝着,她在奥地利的大厅中游荡,她的鞋跟敲打着地板。
“哥——哥……”她叫着,像在呼唤一只走丢的小狗,“你欠我一个吻……美国告诉我了,就是要那样做。如果你在槲寄生下被抓住了,你就要吻我。”门闩轻响了一声,她搜索着角落,发现大厅里没有人。
走廊的中间有一对双扇门。玻璃窗格后面的房间太暗了,看不清有什么。她慢慢地走过去,拿出一把小刀准备着。门把手看起来总是不能如她所愿,但是这一次的事情出乎她的意料。
这房间只有角落里的一盏小灯照明,非常阴暗,房间另一边有一架三角钢琴隐蔽在阴影中。“你欠我一个吻,”她继续说着,绕到了琴的背后。
俄罗斯不在那儿。
她弯下腰,盯着底下。俄罗斯不在那儿。里面?也不在。
她烦躁地瞪着眼。这骗人的乐器,如果它不是那么大而笨重,她就不会想到她哥哥可能会藏在那儿。如果它小点儿的话,就像旁边的那小提琴,或者那边的单簧管,或者……
她意识到自己在一间琴房中。这里整齐地摆放着那么多被完美地擦亮的乐器,奥地利的三角钢琴放在正中间。奥地利他今年没有特别严重地谴责法国,或许那是因为在之后法国已经在忙于骚扰希腊以及塞舌尔,也或许是由于奥地利已经灌下去了一罐啤酒,她不能确定。
她觉得那样一个小小的、前后不连贯的场景滞留在她脑中是个很奇怪的事情:他下颚的样子,不以为然地翘起的嘴唇,严厉的眉毛。他的靴子踏在法国的背上。她苍白的指尖懒懒地在钢琴黑色的光泽上游动。
如果她捣乱了,他会不会谴责她?
她望着她手指在光滑的漆上的反光,以及她小刀的反光,锋利的银色映衬着泛着光泽的黑色。正当她要将刀尖触碰这里,将真家伙凿到这映像的时候——一只手突然抓住了她的手腕。
“怎么回事,”这只可能是奥地利他自己。他厉声道:“你知道你在干什么么?”
她眨眨眼,对上他的眼睛,然后她的心脏突然开始狂跳,甚至她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他一点儿都不像俄罗斯。他的头发是深色的,脸要瘦一些,鼻子更窄,眼睛更偏靛蓝色,并且他抓着她的手腕。他抓着她的手腕,这看起来对他也是一个突然事件,因为他的目光紧张地落在了他们的手上,之后转向还在她手中的刀。而她突然想要逃跑,跑得越远越好,越快越好。她用另一只手抓住刀身,想要解救自己,因为她只了解暴力而非交际,并且这一次是自保,不要管他的钢琴了,那叫他捉住了她。是的,她想,是的,抓着我的手,按住我,把我变成你的,这种愿望那么的突然而强烈,她真的感到她的膝盖因此而变软了。刀掉落在了地板上。
她的血液奔流着,呼吸变成了深深的喘息。奥地利的表情看起来混合着害怕、困惑,以及关心。
“白俄罗斯——”他开始轻轻地说,但是被乌克兰的声音打断了:
“贝拉!”她喊道,几乎是胆怯地样子,从大厅的某一处传来。“我们要走了!俄罗斯叫我来找你。”
有这么一拍他们互相只是看着对方,然后她从他的掌控中弹起来,逃出了大门,出了大厅,她的刀落在了地上如同灰姑娘的舞鞋。
他们开车回家,俄罗斯神经质地谈论着奥地利这里的冬天是多么的舒适温和,而她坐在那儿,在副驾驶座上一言不发。当俄罗斯在路边停下车,并表示自己累了,请求乌克兰接替他的时候,她抓住自己的手腕,并回忆着那弹钢琴的修长手指。
她再次来到维也纳的时候是一月的中旬。她独自一人,并未通报。开门的时候,他眨了眨眼睛,难以掩饰他的惊异。
“白俄罗斯,”他说。他衣着随意——对他来讲的随意:一条苍白的休闲裤和深绿色的毛衣,带领子的衬衣和领带。她注意到,那领带还用了一根领针固定着。俄罗斯从不用领针。俄罗斯有段时间几乎不戴领带。
“我来这里是为了拿回我节日时落下的刀,”她开门见山地宣布着。
“啊……是,”他说,回想着,“我本想用邮件寄还回去。”“本想”,但三周之后还没去做。他们互相看了一阵。“您是否愿意进来?”在这种尴尬的情况下,他后退了一步,指着他家的前厅。
她只犹豫了一下子,便走了进来,她的漆皮鞋踩在门槛上。她穿得不错,穿着黑色条纹的长筒袜和有白色蕾丝的裙子,海军蓝的大衣以及鸽灰色的手套。并不是说这有多么重要,这和她平常所穿的也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我能拿您的大衣么?”他问。
“不。谢谢,”她冷淡地说道,而他礼貌地点了点头。
“好吧,”他说道。“如果您不介意在这里等一会儿,我会把它给您拿过来。”这次轮到了她点头。他离开了,在消失在某间大厅中。
她在他家门厅中站着,双足并紧,双手在身前扣着,等待着。
他几分钟后就回来了,刀在他手中。他若有所思地将一根手指拂过刀身,而后将它调转过来,刀柄对着她。她接过来,几乎是怀疑地将它检视了一遍。
“你擦了它。”这几乎是个控告。事实上她刚用刀尖指着他的身子中间,这动作并不是个巧合。
“这使得刀刃不至由于生锈而变钝,”他看着她,温和地指出。她不知道他的话是否是个挑衅还是单纯的声明。过了一会儿,她抬起下巴,调转脚跟,一言不发地推开了他家的前门。
“欢迎再来,”他说道,声音还是那样的温和,但这次在声音中或许有着些许的欢愉。她已经走上他家覆盖着积雪的步道。
她回头望向他家纤细的门框,他的手在口袋中,他戴眼镜的眼睛看着她离开——她瞪了一眼。
她曾经爱过基辅罗斯,像一位女儿爱父亲那样爱着他。当蒙古在迦勒迦扫荡而过[1],并用箭射穿了他的胸膛的时候,她尖叫着,尖叫着,尖叫着。
乌克兰把她放在俄罗斯的臂膀中,并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而她作为他们之中最年幼而弱小的,抓着她的哥哥,因为他是最高大而强壮的。
蒙古在十五年后回来,将他们打倒并分开。立陶宛找到她[2],将她带回。当他使用她自己的语言试图叫她发笑的时候,她也紧紧地抓住他,像一只锁链断掉的锚,抓住深海的黑暗。
“哥哥,”她有一次对他说,“你为什么有时间去访问在远大洋之中的冰岛,却没有时间来看我——这个就住在你的旁边的人?”
俄罗斯试图把他的大块头缩进角落,并尴尬地一笑。“我刚好有个晚餐——刚好有个商务晚餐!”他说着。当她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头贴在他胸膛的时候,她感觉到他的心跳加快了五档。“我——我会和你一起去晚餐,好吗?”他试图这样说,而她抬起头仰望着他,希望写满了她整个脸。
“真的?”她问。
他剧烈地点了点头。“在下一个世界会议后。我会和你在酒吧见面,就是英国总喜欢去的那家,好吗?”
她用手臂抱住他,为此他发出了一小声紧张的尖叫。她闭上眼睛安祥地耳语道:“好的。”
那会议来了又走。她站在酒吧中,就是英国总喜欢去的那家。普鲁士已经开始喝酒了并且试图去打架,法国表示若是裸体打架的话他会同意的。德国勇敢地试图保持他哥哥的衣服还在他身上。美国在给匈牙利讲什么故事,他做着活泼的手势,而她明快地笑着。奥地利在喝酒。
俄罗斯不在那儿。
俄罗斯从来没在那儿。
她怀疑自己疯了。
当然,以前曾有一些谣言小心地在她背后说她疯了。俄罗斯在逃离她的迷恋的时候,也不止一次粗心而又恐惧地把它说出来。但这是第一次,她开始思考这个传言中也许有对的部分。若非如此,她怎么会冲进奥地利的房间——奥地利,一个她几乎不认识的、之前也从未注意过的国家——而唯一的意图就是被他抓住?
她滑进他家一层的一扇窗户,进入一间未开灯的不熟悉的后厅。她把她的裙子拉直,关上窗户,然后出发。几分钟后,她听见一扇门关上了。脚步声随之而来,朝向她的方向,并突然在旁边的一间大厅停住了。
“谁在那儿?”他问道。她怒视着弄出了如此大声响的地板:难道不知道音乐家有着很棒的听力么?并且说到这个,哪里才是他的音乐室?
“普鲁士,是你吗?”他的脚步声继续着,步子变得快而坚定。他越发恼怒:“普鲁士,我发誓,如果你再一次在我的短裤上写下侮辱的东西……”
不要再试图保持安静了!她猛冲向另一个角落,然后听到他开始跑着追了过来。她跑过大厅,看到了音乐室开着的门,也听见了他的长腿将要追上她。她跑进来,转身,将刀威胁地指向他的三角钢琴。奥地利正好滑进门口,并及时地停下。
他穿着三件套,不过没穿西装外套。白衬衫,灰裤子和马甲,勃艮第红的领带,黑鞋子。他看起来像个教授,或者是个图书馆长,这显然不像是俄罗斯的风格。
他的目光闪烁在刀刃和她的脸上,而后转到刀刃和他的钢琴上,最后定在了刀子上。他的嘴试图说些什么,而她几乎想要为此发笑——因为他爱他的音乐甚于害怕她:这在某方面讲真是有趣,因为所有人都怕她,即便是俄罗斯,特别是俄罗斯,并且有的时候他的拒绝确实叫她想要大喊大叫并把什么东西撕成碎片。
她猛冲过去,而他也同时这么做了,抓住了她的胳膊然后旋转她就像在跳某种扭曲的舞蹈。她的后背撞到墙上,而他用身体努力地使她固定在那儿,他的手试图从她的手指中扭下那把刀。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感觉,被他和墙挤压着,这叫她的拳头足够松懈,使他得以从她手中夺走那武器。他把它扔到远得够不到的地方,刀子掉在了覆盖着大部分地面的地毯上。而后他从她身前退了一步。
“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他开始发怒,并把马甲拉直——但这还没结束,因为他已经离开她了,而这是不够的,是不够的。于是她再次跳向他的三角钢琴,掏出了第二把刀。他从后面抓住她,把她拉向自己,手指令人疼痛地掐入她发起攻击的那只手的前臂,哦,既然他现在是这样有力的话,如果她真做了什么破坏后会变得多么有力?
她屈起一条腿,勾住他,想使他的脚失去重心,而他试图抓住她的腰带,解开那带子并拽倒她。她绝望地倒在了键盘上,他抓住了她的脚踝,将她拖离那里,而后她发现刀子已经被扯离了她的手指,她的后背被猛地推向地板,胳膊固定在头的两侧。就这样,他伸展着她,小腿和皮鞋固定住她的腿,而她变得无法呼吸。
他的胸膛也在起伏着,头发乱了,眼神冷酷。他无情地抓着她,耐心已经消失。他用一只手将她的手腕固定在她头顶,另一只手梳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整理了领带,而后嘴唇紧闭,陷入了可怕的安静,开始搜查她身上是否还有其他的武器。她的胳膊,她的身侧,腰上的腰带,裙子口袋,她的腿——然后,布料之下的刀柄泄露了秘密,他停了下来。他的表情变得阴沉,眼神对向她的。
“您会原谅我的,”他简短地说着,以一种有些嘲弄的方式倾斜着头。而这是真的——她将会原谅他的,因为这不是一个礼貌的请求;这是一个宣言,甚至是一个命令。
在他的手伸入她的裙子的时候,他一直和她保持着目光的接触。这叫她的呼吸打结了。在一阵直率的搜查后,他从她的长筒袜顶端扯出了两把刀子——一条腿一把,并把它们扔到了其他那几把的方向。在确信她已经被缴械了之后,他把裙子尽可能地盖回原处。他没有道歉,并且看起来并未准备要放走她。有一阵,他只是这样呆着,安静地看着她,好像在思考将要拿她怎么办。她的呼吸变得急促,而这对他们现在的状况毫无用处。
“能否告诉我,您为什么持续地针对我的钢琴?”最后他问道,靛蓝色的眼睛盯着她的,她咽着口水,脉搏在他的掌心下跳动。
“因为你一直追着我,”她小声说着。他为这个招供眨了眨眼,他看着她,唯一的声音就是他们的呼吸声。
“你曾是个帝国,”她说。奥地利的眉毛轻蔑地挑起。
“那是很早以前。”
“你一定怀念那时。所有那些权力。”他的手指抓紧了她的手腕。她的胸膛起伏着,呼吸变得短促,她继续说着,空洞得如同说给她自己听,“北意大利说你曾经把他踩在你的靴子下,如果他要试图造反的话。而当你养育他的时候还将他捆在树上——”
“别诱惑我,Frau Weißrussland。”这些词语被咬字得十分清晰并充满威胁。用他的母语德语念起她名字的声音,使得她从脊柱到最核心都得到了一阵战悚。她没有听从他的建议,而是小声说——
“为什么不呢?”
过了一拍,他的眼神闪烁,嘴唇抿起来。在这警告之后,他的嘴唇倾向她,如此的强硬并且充满惩罚。他的手指抬起她的下巴,将她的嘴唇对准自己的,强迫分开,并贪婪地探索着。当他感到满意了才停下,将她的头转到一边,饥渴地将嘴唇贴在她的脸颊上,并滑向她喉咙的皮肤。“你很美,”他小声说着,好像他拥有着她,而她颤抖着,急切地向他的触碰投降。
“奥地利,”她喘着气,只是为了感受他的名字在她舌头下尝起来有多么不一样。
他把她从地板拉起来拥进怀中,手指插进她的头发,并向后拉着她的头,这使得她别无选择地看着他。“‘先生’,”他坚定地纠正着,“你应称呼我为‘先生’。”她发誓她的嘴为这些话而湿润了。
她咽着口水,眼睛充满爱意地望过去。“是的,先生,”她说。他又吻了她,手还在她的头发中,另一只则有力地从她的后背向下滑,手指分开,将她的髋部压向自己。她自己的手,之前暂时搭在他纤瘦的肩膀上,痉挛着抓紧了他,现在充满渴望和需要,向下摸索着来到他的精瘦的躯干,摸到了他的皮带和裤子以及——
她所知道的下一件事,就是她被猛地拉过、脸朝下倒在他的大腿上,他的手臂将她再一次定在了地板上。他翻起她的裙子,当他拍打的时候她倒抽了一口气。
“我有没有给你触碰我的许可?”他问道,而她热切地眨着眼,她臀部的一小块发痛着。指挥棒,她想。那不是他的手,而是指挥家的指挥棒。
“我——我只是——”又是两下。她这次确实呻吟了,她的后背淫荡地拱起来。
“我有没有给你许可?”他重复道,声音更强硬了。
“没……有,”她颤抖地说出来。他打了她第四下,而后她自己纠正了,“没有,先生!”
“现在。当你做了一些错事,该怎么办?”指挥棒的尖头放在她身上,等待着。她咽着口水,眼睛闪烁着欲望。
“我很抱歉,先生。”为了得到更好效果,她马上补充道,“这不会再发生了。”
又是一拍,而后指挥棒离开了她。“很好,”他说,听起来很满意。有一阵停顿,在一些轻微的挪动、衣物的沙沙声之后,她手腕上的手指变成了他的领带。他把它系紧,并绑在了钢琴的一条腿上,而后退回来,好像在检查他的手工。
她的裙子还是掀起来的,他的手掌划过她的后部,搔弄着象牙白的皮肤遇到白色蕾丝的地方,漫无目的地扯着她的吊袜带。“现在没人穿这个了,”他伤感地叹息着,“至少不是像它们原来的那样。”他寻觅着她灰色高筒袜的顶端,深入其边缘,又从她大腿的顶端附近再伸出,这得到了她喉咙中的一声呜咽。她在他的腿上无助地扭动着。
哦,求你,她想这么说,而咬着嘴唇防止自己说出来。
就好像他读了她的心,他折回放下她的裙子,手指来到了她的腰带,解开它剩下的部分,而后是裙子背后的纽扣,以某种方式试图优雅地把它从头部那边脱下来。而它在她胳膊那里打褶,成了一团混乱的饰边和蕾丝,没法完全地脱下来。“转过来,”他命令着,并且——显然不是很容易地——她做到了。系着她手的领带被扭得更紧了一点,她的血液也又升起了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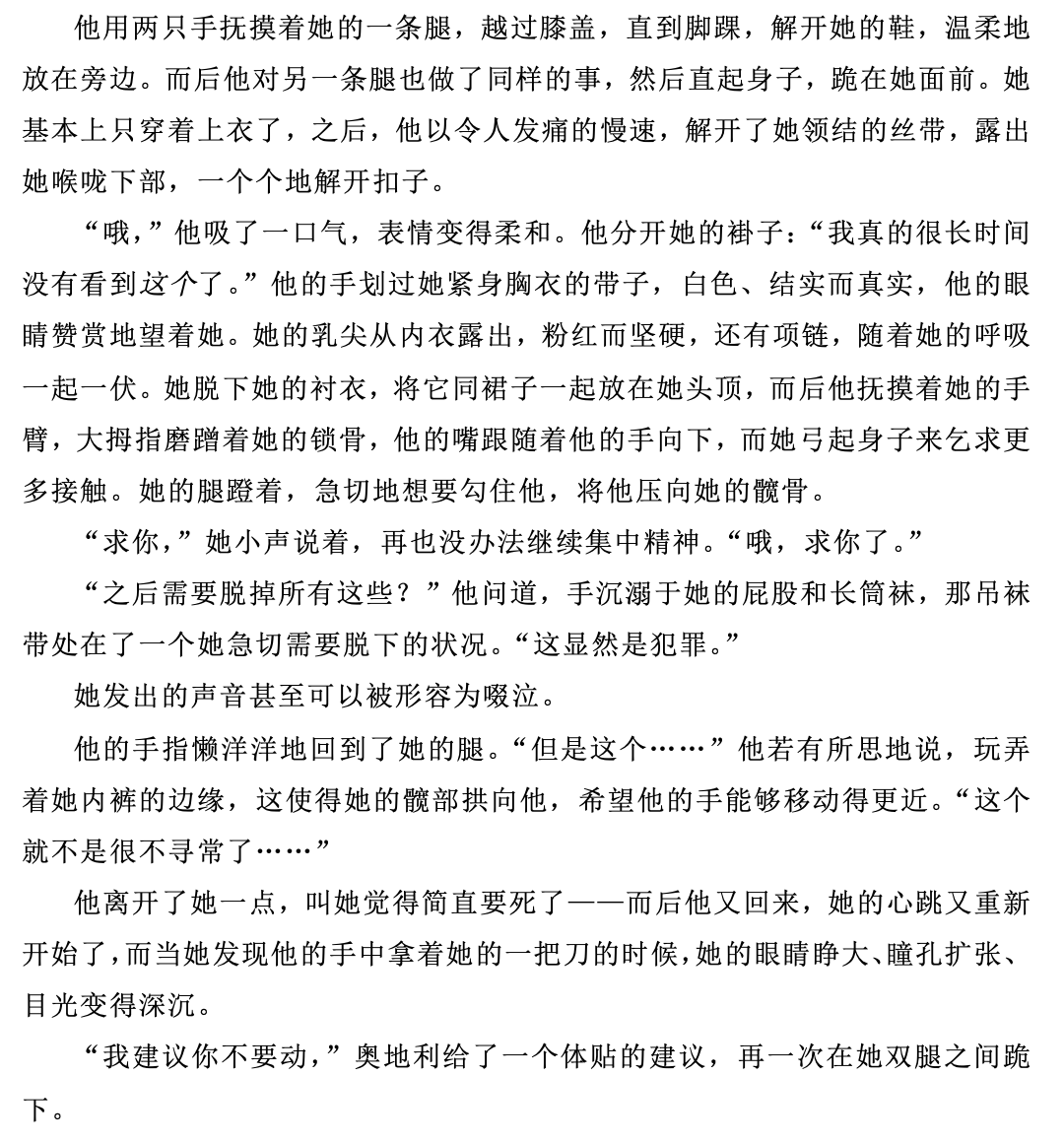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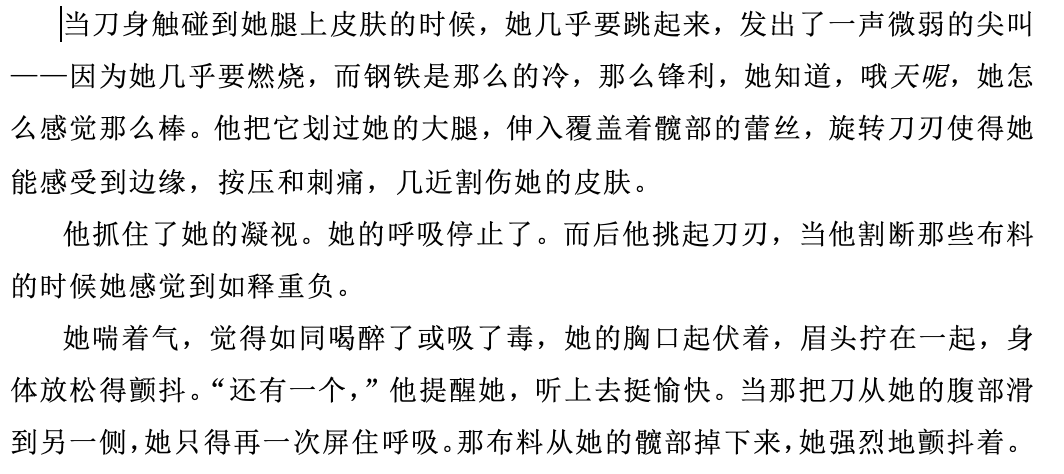
“求你,”她喘息着,绝望而欣喜若狂,没办法得到足够的氧气。“哦天呢,求你,求你,求你……”
他移走那些已经成为碎片的棉布和蕾丝,轻微地抬起眉头,审视着她的状态。“好的,”他简单地回答,把刀放在旁边。他摘下他的眼镜,叠起来,放在钢琴上。而后他坐回来,开始解开他的衬衣袖口,把它们卷到前臂上,并闲逸地望着她。她在他的视线下颤抖着,就那样克制地、半luo地躺在他面前,请求着。
他移动到她上方,如此令人着急的接近,她能感受到他衣服的摩擦,他皮肤的热度,并且几乎——几乎,但是那么无情地缓慢——感受到他身体的重量。她在他身下扭动着,想要把自己贴上他,但是他只是将自己远离她的触碰,她因此想要啜泣。
“‘求’什么?”他在她耳畔耳语,令人折磨地无辜。
“把我变成你的。哦天呢,求你,把我变成你的。”
一阵皮带扣的咔哒声,布料和皮革的移动,之后他将自己对准了她,触碰着但是并未进入,而她几乎就要到极限了,仅仅因为这微弱的接触使她喊叫出声并仰起了头。
“看着我,”他对她说,她听从了,眨着眼睛努力聚焦。他又一次抓着她的下巴,手指紧扣着她的下颚。“我不希望你在假装你在和什么别的人。听明白了么?”
他是如此强势,如此甜蜜而冷酷,使得她想要亲吻他。“是的——”她几不可闻地哽咽着。“是的,先生。”他终于进入了她,深而剧烈,她不由得弓起背部,她的眼睛眨动着紧闭,同时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尖叫。
他的手指坚定地按下她的下巴。“我,”他提醒她,他的眼睛闪烁着占有欲,“我的。”
“你的,是的。”她耳语道。
他吻着她,他的舌头索要着她的嘴。而后他开始动,索要着她其他的部分,他的手——他美味的、灵活的弹钢琴的手——划过她的身体,有时候温和而充满爱意,而后又尖锐而强制,拍打、撕扯着每一处他可到达的地方,使她发出声音如同屋中其他的乐器。
在这时候,他拥有她,而同时,她喜欢他这样。
这成为了某种例行公事。
她本不想这样的。她真的不确定她第一次来到他房子是为了什么,但是却可以说她本来不想第二次来这里——或第三次,或第四次,第五次,甚至第十次。
在之后,他松开了她的手臂,温柔地按摩着她酸痛的手腕,将她疲劳、颤抖着的身体放到他的腿上,把她的头发梳到耳后。之后她一定是陷入了睡眠,因为她转天早晨醒来时是在一间客房,她的衣服干净而平整,刀子整齐地摆放在旁边。她并未试图寻找他,就离开了,因为这只是一夜情;他不是俄罗斯,他无关紧要。
但是俄罗斯始终拒绝着她,有时候他跑到立陶宛那里,或者中国、美国,而她有时发现她自己在奥地利那儿,被系在他的床上,或者弯在他的钢琴上,求着他去充满她。
那是在另个世界会议之后。在另一个世界会议后,她想同俄罗斯一起回家,但是当她从卫生间出来后,看到了只有德国和奥地利,从空荡荡的会议室中走出来。他们看到她的时候停下了,后者温柔地眨了眨眼,前者则不安地僵硬着。
“俄罗斯在哪儿?”她问着,因为他曾说他要留下,他曾说他要等着她。她的手抓着裙摆,抓着布料里面的刀。
德国清了清喉咙来掩饰他的不安,嗫喏着一个非常迅速的再见和道歉,然后溜走了,表示自己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奥地利为他邻居的逃跑而干巴巴地扬起了一根眉毛。
“我听说他跟着意大利兄弟去他们那儿了,”他最后回答道。“你知道,他很喜欢他们。”他看着她,或许带着些嘲弄。她冷酷而暴躁地瞪视着他,渴望着把他的定制西装切成碎片。
“我听说你的前妻挺喜欢美国,”她回击道,决定不用她的刀,就只这一次。“她有次和他骑马约会。”
他的嘴痉挛了一下子,即使很微弱。他吸着气,推了推眼镜。“在大厅的尽头有个衣柜,”他提醒道,扯下他优质皮革的手套,望向他所说的方向,“非常结实的柜子。”
她抑制着自己不要抓着他的胳膊跑过这个走廊。
Fin.
作者的话:Omg。这真的是我写过的最色情的东西。我太羞耻了。OTL。(但是LOL,哦,奥地利啊。谁在乎她有些疯狂;她既漂亮又优雅,并且还叫你和她玩帝国的游戏。有时我也这么想你。)时间会证明我或许会喜欢这个,但是现在来说,我已经受够它了,只想把它贴出来,清出我的脑子。
并且,是的,紧身胸衣通常上需要与内衬一起穿,否则身上会有红痕甚至擦伤,但是不管这个了反正也没有系得很紧而影响了行动,并且可能有内置的内衬。因为那确实存在。并且,任何通常穿着高筒袜而不是连裤袜的人都知道,明智的方法是把内裤穿在系带之外,而不是在里面,不过,嗯……或许白俄罗斯脑子有梗?或许她选择这么穿是为了性感?(因为真的,穿在外面会更方便,里面会更性感,并且——这只是个色情小说好么快别管我了。)(译者说:不知道我又没有翻译清楚,脱衣服那一段,之所以会用到刀子,就是因为她把内裤穿在了吊袜带里面,为了脱掉内裤而不用把高筒袜脱下来,所以直接用刀把吊袜带给割断了。)
另外一方面,这个故事来源于一个2009年的旧的、没被完成的kink meme请求(当我在搜索这个CP的时候发现的),请求奥地利X白俄罗斯。它大概看起来是这样的:“奥地利由于白俄罗斯抱怨俄罗斯不理睬她而感到厌烦,开始命令她,因为他是个贵族而且那样高傲。白俄罗斯迅速地服从了,因为那是她想从俄罗斯那里求之而未得的。”如果你恰巧写了这个请求,在很久之前,那么……请你欣赏?
这故事的其他部分是由于我事实上对这些情节情有独钟:1)选择一个有crack的假设或者CP并进行严肃的创作,2)脑袋不太正常的角色,3)阴暗的,情节相关的性。
我很快会回到历史向的小说中的。DX
编辑:我意识到,“Fraülein”现在是个比较古体的、贬低的头衔,既然这故事发生在现代,我还是把它换成了更合适的“Frau”。我要为这个错误道歉。
作者为题目的解释:
本题目“白马”有着多层的意义。在基督教神话中,天启四骑士中的“征服”骑的是白马,其征服的含义或许可以本篇中奥地利和白俄罗斯的“命令/服从”关系相类比。另外,在英语中,“白马”也是毒品的俚语,这与奥白俄之间不健康而令人上瘾的关系也有相似之处。除此之外,“白衣骑士”“银甲骑士”这样的浪漫幻想也总是离不开白马,由于其纯洁、英雄的动物形象。而这个故事其实也有些幻想的意味,有两方面,一是白俄她希望得到的(也就是俄罗斯,特别是她想叫他成为的),一是她真正得到的(也就是奥地利,他可能是白衣骑士的反面形象,因为他的礼貌和王子般的态度,而性格中却有着巨大的阴暗面)。最后,这也影射着Belarus的直译就是“白色的俄罗斯”。
[1]译者注:指1223年蒙古与钦察人及基辅罗斯的战争。迦勒迦河为第聂伯河的下游。在此,基辅罗斯和钦察人的联军被蒙古人打败。这是蒙古入侵的第一战。
[2]译者注:应指立陶宛大公国(Grand Duchy of Lithuania)时期,自1320年起,已经被蒙古打得七零八落的西罗斯的公国均向立陶宛称臣或被吞并。此时白俄罗斯领土全境、部分乌克兰领土均并入立陶宛大公国。在白俄罗斯地区通行的鲁塞尼亚语(Ruthenian,为一种东斯拉夫语,被视作现代白俄罗斯语、乌克兰语等的前身)被迁移到此处的立陶宛贵族接纳,成为立陶宛公国记载文件和书写的主要语言。
2014年11月